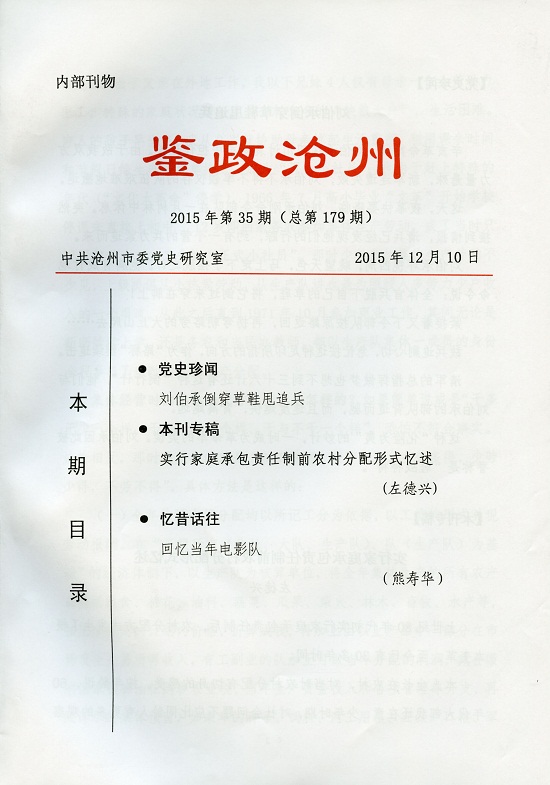
【党史珍闻】
刘伯承倒穿草鞋甩追兵
辛亥革命期间,刘伯承在四川讨袁新军中担任连长。由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新军连遭失败,刘伯承不得不率领仅存的队伍艰难地撤退。
这天,夜幕快要降临,刘伯承刚命令部队在一片树林中休息。突然接到情报,清兵已经发现他们的行踪,约有一个营的兵力紧追而来。
刘伯承环视四周,眺望天色,马上定下了摆脱之计。他胸有成竹地命令说:全体官兵脱下自己的草鞋,将它倒过来穿在脚上!
紧接着又下令部队按原路返回,再拐弯朝路旁的大丘山爬去……
敌兵追剿心切,急忙按这种足印所指的方向,作为“路标”继续追击。
清军的总指挥做梦也想不到三十六计还有这种“倒行计”,他们与刘伯承的部队背道而驰,而且速度越快,背离越远。
这种“化险为夷”的妙计,一时成为革命军的美谈。刘伯承因此被誉称是“鞋战神将”。
【本刊专稿】
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前农村分配形式忆述
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分配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至今已有30多年时间。
本人生长在农村,对当时农村分配有切身的感受。按年龄说,60年代大部我还在童、少年时期,对社会问题不应比同龄人有更多的观察和记忆。由于父亲在外地工作,我以下兄妹4人仅有母亲一个女劳动力出工,特殊的家庭状况曾一度是全村有名的“缺粮大户”,生活困难。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从9岁就协助母亲挑起生活重担,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给生产队打草挣工,成为“课余小社员”;也由于赶上特殊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停学),1966年7月高小毕业“文革”开始学校停课未直接上初中,12岁即回家务农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成了当时只记男整劳力40%工分的“正式小社员”。那时少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少见,上级提倡从小热爱劳动,从生产队讲也是为照顾人多劳力少户收入的一个渠道。从此之后直到1971年10月参加商业工作,其间无论是断断续续上学,还是务农和当民办教师,都以生产队集体一成员的身份全程参与了当时的农村生产分配。
集体经营时的具体分配方式究竟是怎样的?如果简单说成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恐怕不符合事实。恰恰相反,那时最坚持的就是“以工定酬,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具体方法是这样的:
(一)全年的预决算分配均以所记工分为依据,以工值的形式兑现劳动报酬。在“三级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队(生产队)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下,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将全年集体生产的所有农产品包括粮食、棉花、油料、蔬菜、瓜果、柴火、林木、畜牧、水产等,按国家规定的计划内价格,折算成钱,再加上由以上产品中一部分在市场发生交易所得收入,有工副业的队加上可做当年分配的利润,减去缴纳国家粮棉油征购和农业税、当年生产资金投入和各项管理等开支,再做详尽的集体预留,如来年的种子、饲料、河工用粮、五保户口粮、军烈属补助、社务工支付、集体储备之后,是社员当年可分配并以工分值形式兑现的劳动报酬。简单说,就是当年做了各项扣留之后全部分到社员手中的产品,以国家计划价格算出总价值,然后以工值的形式逐户兑现劳动报酬。这些总价值,除以全年总计工分,得出每分工的单价(以满工10分为计算单位),然后以户为单位,计算和支付劳动报酬。大体分三步:第一步,将各户的工分计算成现金总额,作为全年应得报酬。第二步,将各户各次分到的农产品计算成现金总额,作为已预支报酬。第三步,将全年应得报酬减去已预支报酬,即为各户决算分配的结果。正好相平的,为“平粮户”(实际应称“平款户”,当时以粮称谓,与以下“余粮户”、“缺粮户”称谓统一),说明该户在生产队投工的价值与从生产队分到产品的价值不多不少,既不用给投工多的户补钱,又不从投工少的户得钱。这里需说明的是,事实上绝对的分文不余不缺基本没有,只是大致相等,或是在相差无几的情况下,通过在生产队分东西主要是瓜果蔬菜时与对冲户议好多要或少要一些找平;投工报酬大于已预支报酬的,为“余粮户”,也叫余款户,说明劳动成果中还有一部分没有领到家,暂时被劳动少的户领走,也可视作短期为其做了垫付,但不是白白付出,而是要在决算后以现金的形式领回,投工报酬大于预支报酬多少钱,就叫余多少钱,就领回多少钱,但这些钱不是由生产队集体支付,而是由“缺粮户”给付(由生产队办理);投工报酬小于已预支报酬出现负数的,为“缺粮户”,也叫超支户、透支户或欠款户,说明已暂时透支了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应在决算后以现金的形式偿还人家,负数是多少钱,就要给“余粮户”拿多少钱。当然也是交生产队办理,个别如有本家族或私交好的,经双方自愿,也可与“余粮户”结对对冲协还。决算一般分夏秋两季进行。夏季在分了新小麦之后,叫预决算,兑现一次余缺款;秋季在秋粮秋柴秋果及其他秋收作物和大白菜等全部分到户之后,再进行一次总决算,彻底兑现全年余缺款。生产队在对当年农户分配上,全部用余缺户相互间还余补缺求得平衡,不发生用集体粮款为“缺粮户”支付超支问题。
各生产队由于劳动力和人口比例、构成不一,“余粮户”、“平粮户”、“缺粮户”的比例也不尽相同,有各占三分之一的,也有四二四、五一四、四一五、三一六的,也有无“平粮户”,只“余粮户”和“缺粮户”两种的。而且比例是动态的,每隔几年甚至每年都有变化。具体到每户,也是这样。这是因为有的整壮劳动力步入老年,有的由少年进入青年,工分相应减少或增加;家庭成员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分家单过的、生老病死的、内娶外嫁的、参军考学招工的、迁出迁入的,在家庭“余缺户”转化上体现得非常现实。比如我们家,整个60年代都是“缺粮户”,每年夏秋两季给“余粮户”拿少则150元,多则260元的现款。1970年我的全天工分增长到7.5分,而且受大队委托参加了县五七中学长达8个月的县机电班培训,10月份我又担任民办教师,等于除我母亲之外又添了一个妇女整劳力,加上大妹打草、干活挣工,变为“余款户”,当年决算收到37元余款。次年我教书,即使仍记男半劳力工分,又余140多元。但无论各户怎样变化,当年决算生产队归零(不赔不赚),只在余缺户之间填平补齐、自求平衡,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二)生产队在产品分配中工分占到一定比例。决算是以现金找齐,平时产品分配数额的确定则是以人口为主,而工分也占到一定比例。因为所分配的农林牧渔产品,全部按国家规定的计划价格计算,比集市贸易价格低百分之五六十乃至七八十。如粮食,正常年份玉米和小麦市场价为0.33至0.50元之间,而计划价格分别固定为0.08元和0.105元;蔬菜也是这样,以茴香为例,市场价一般在每角1到8斤之间,我们生产队固定为13斤。如果全部按人口分配,人口多孩子多劳力少工分少的户多沾光,人口不多孩子不多劳力多工分多的户会吃亏,不尽合理;如果全部按工分分配,既不符合土地等资源集体所有、农村户口人人有份有权共享的公有制原则,又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社会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的制度优越,因此上级提出了“人八劳二”的大体分配原则,就是人口占80%,工分占20%。具体方法是:在每次产品分配之前,以上年末的各户现有人口及工分为基数,按以上比例算出人口和工分各自应分的绝对数,然后相加,即为本次或本类产品分配的数额。后来几年有的突破了“人八劳二”的比例,改为“人七劳三”,有的除粮食之外,对其他农产品的分配甚至改为“人六劳四”、“人五劳五”,等等,以调动社员投工劳动的积极性。
关于粮食分配,一般坚持“人八劳二”,最低不能突破“人七劳三”,这是硬杠杠,不能随意更改。因为粮食是国计民生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是关系人们吃饭、生存需要的第一位资源。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猛发展工业和科技教育文化事业以及建设强大的国防处处需要粮食,而农业本身又是弱质产业,当时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农机化肥严重缺乏,粮食生产还不过关,对粮食的统筹则是党和国家所关注的第一件大事。因此,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全国各行各业人口实行定量供应,农村人口按平均一天一斤粮食分配,多生产了不能多分,按计划价格交售给国家,以保证非农人员供应,实际是“以农补非”;赶上歉年,国家再按口粮返销给社员,实际上是以丰补歉的调节功能。平均每人每天一斤并不是固定按人头定量一斤,而是按“人八劳二”或“人七劳三”的比例分配。工分最多的,全家每人可吃到1.2斤或1.3斤,没工分的,只吃8两或7两。这能体现多劳多得,同时也拉开了收入的差距。除口粮外,另有每人2分的自留地,“文革”期间统有集体耕种,每人每年大约分30到40斤粮食,一般不占口粮指标,但计入工值分配。此外,生产队除生产小麦,玉米,红、白、多穗、杂交高粱,谷子、大豆、红薯等主粮外,还种植主要是套种一些杂粮,如绿豆、豌豆、黏谷子、黏高粱等,每人每年也能分10到20斤,有的队不计口粮,但无论计不计口粮,都计工值。
从总体上说,那个时代不管分得多分得少的,粮食都不富裕,许多户需到集贸市场买高价粮补充,还要用大量糠和野菜辅助,否则难以吃饱。但各户缺粮(这里指实分粮食与实际需要的差距)程度不一。按说,“余款户”因劳力多出勤多吃得多,又少有婴儿孩童给均匀,应该说最不够吃,日子最难过,其实大部不然。这是因为,他们不光分得多,而且有劳力出河工,每年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春冬两季前后6个月在外治海河,全部吃国家和集体的补助粮,省下自家的口粮;此外,决算有余粮款,有钱买市场粮。所以相对其他户来说,劳力多的户日子要好过一些。超支户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人多劳力少而且人口多为婴儿和幼童的,分粮分得少,但吃得也少,可省出一部分到市场出卖交超支款,而且所分其他经济作物如我们队的小枣、瓜菜等,也可拿出一部分到市场出售换钱,生活还能过得去。但另一种情况则最不好办,这就是人多劳力少,孩子还大都是10来岁、10多岁正在上学的户。本来没工分分得少,但吃得不少,当年夏秋决算后需交超支款,来年开春还得买高价粮,是双重生活困难户。
由于人均口粮限制得很死,春季缺粮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旧社会农民有“秋好挨,冬好过,最难受的春仨月”;“麦子黄梢,饿得蹬脚”之说,此时虽有本质区别,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但粮食定量的概念,不是现在一些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天只允许吃多少,不允许多吃,因此挨饿,而是按计划价格供应部分有数量限制,不足部分可以到集贸市场买计划外价格的私粮补充。集市贸易的粮食市场春冬两季是常开的,私人之间粮食交易也是常有的,不过都比计划内价格贵几倍。有钱的不犯愁,没钱的就得借账。国家每年春天还要下拨大量的返销粮、救济粮和救济款,以保证人们都能吃上饭。
为多占一点计划内粮食指标,与1958年“大跃进”时一些地方胡吹产量相反,一些生产队在产量上打埋伏,有的搞点儿瞒产私分。上级虽然也一再整顿,但体谅群众实际困难,并没有听说真正追究过谁。私分不是不计价格的白给,否则出工多的户有意见,还是“人八劳二”或“人七劳三”,还是进入工值决算,只是生产队设两本账而已。当时各地大种红薯且当主粮,既因红薯是高产作物,亩产可达4000斤,4斤鲜薯折1斤粮,营养比1斤粮还高,还有一层秘密在于,在折算口粮时可以打马虎眼,上级不会较真。但决算计入工值则是必须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社员全年从集体中分得的所有农产品,都是按计划价格作价计算工值,按实挣工分进入决算的。(2)农产品分配数额,除粮食外,其他全部取决于当年的实际收获;而分配的依据,包括粮食,均以人口为主,但作为付出劳动的尺度工分也占了一定比重,尤其工副业可分利润,一般全部按工分分配。(3)作为农民主要劳动成果的粮食,劳动者没有全部分到,给缺劳户承担了部分口粮是事实,但缺劳户又以计划内的价格给付了报酬,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国家限制了分配数额,相当一部分交给了国家,留在了集体。
工分是怎么得来的?工分构成大体有四:一是劳动投工。这是最主要的部分,在全年总工分构成中占80%到90%。二是投肥。各户向生产队投交的人粪猪粪羊粪鸡粪、垫圈土加野菜野草积沤的土肥草肥,以及拆扒的旧房旧炕旧烟囱旧锅台,等等,按肥力等级定出工分,以车或方计分。三是投草。生产队一般养有二三十头牛驴等牲口供使役用,条件好的还养有骡马,常年所需饲草除集体预留秸秆和种苜蓿外,就靠各户打野草交鲜、干草解决,这也是解决有少年儿童缺整壮劳力家庭工分少问题的一个渠道。投草按品种质级以斤计分。四是照顾工分。这部分比重很小,主要是对军烈属的照顾。
这里主要说投工所记的工分。先说工分的评定。将全队所有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成员,包括男女老少,按年龄、身体状况、从事农活的技能和熟练程度,由队委会大体划出三种类型:一是男女整壮劳力,一般男在20至55岁之间,女在20至45岁之间;二是男女半劳力,一般男在16到19岁之间和56到65岁之间,女在16到19岁之间和46岁到55岁之间;三是男女辅助劳力,这部分包括除去上两项人员以外,所有自愿要求并且身体条件能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各年龄段人员,即老头老婆、辍学少年。在以工分为谋生主要手段的时代条件下,家家都挖掘出工潜力,多挣一分是一分,尤其人多劳力少的户为少拿缺粮款,更为迫切。只要这部分人要求出工,生产队都给安排力所能及的农活。
劳动力类型划定之后,再确定每个人出一天工的具体工分。男整壮劳力标准工是10分,半劳力是7.5分,辅助劳力是6分及以下;女整壮劳力是7.5分,半劳力6分,辅助劳力5分及以下。但这仅仅是标准工,还要因人而异。比如,男整壮劳力要求“上河打堤、拔麦子脱坯、提耧下种、使牲口耕耙地、拾麻袋扛口袋、扬场簸簸箕”各类技术活力气活样样能干,达到的记满工,达不到的,视具体情况削减1到2分。相反,有些年龄虽然超过界段,但仍身体强壮,且农活技术过硬,有的还属专门技术强、稀缺性的,如养牲畜、种菜园、播种子、泥房屋等,则适当增加1到2分。出工一般为一天三出勤,即早晨、上午、下午,全天工分也分到三次出勤上,如我挣7.5分时,早晨记1.5分,上、下午各记3分。
由队委会(队长、副队长、会计组成)定工分的传统做法,一直实行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被上级推广的大寨“自报公议”经验取代,每人应得多少分,由自己申报,全队社员集体讨论,提出意见,最后举手或者投票决定。
定下相对固定的工分之后,也不是僵死、固态化地照记工分,除了岗位、工种相对固定人员如饲养员、种菜员、教师、赤脚医生等,以及另有考核标准的治河民工、工副业人员,其他临时派活人员一律以当天出勤时点、劳动态度、完成任务快慢、质量效果优劣等决定工分照记还是增减。以队长的钟声为号,前后不超过大约半小时,必须领活下地或到指定地点开始劳动,否则要扣工分;到了饭时队长、副队长以及其他临时带班人发话收工才可收工,无命令早走的要扣工分;风雨打搅、临时有事晚到早离的,要扣工分;干活不积极,被别人落下一大块的,要扣工分;因不努力没有按时完成任务的,要扣工分;干活不认真、质量不行,如耪地“猫盖屎”、“草上飞”(形容锄头只划破地皮,入地不深),刨玉米秸、高粱茬“扦笔管儿”(形容镐头只砍外露部分,不深刨根部),铡草“噎死牛”(形容按铡刀不到位,草有连刀),被队长检查发现,或被同伴揭发的,要扣工分,等等。与此相反,到得早、走得晚、完成得好、活干得出色的,多加工分。一般是晚饭后记工。队长副队长在场,平时一家一名报工人员聚集,隔三差五全体社员集合记工、开会、学习“一揽子”,按居住方位排序,逐家报其家庭成员今天在生产队干了什么,出工有无耽误,完成情况如何,和谁在一起,有谁证明,队长认为符合事实,记工员就按原定工分记分,队长认为不符,就说明情况并拿出减分意见,报工员本人或其家庭成员如提不出反驳理由,记工员就按减后的记分;如提出反驳,则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对质,甚或召集全体社员公议,议定并落实当天究竟应给记多少分。至于表现突出、干得出色的,也由队长或知情人员提出,记工现场议论,当场决定并落实增分。所以,现在说那时在生产队干活是人人“磨洋工”、集体偷懒,不尽符合事实。想偷懒起码过不了队长当面批评减分、大家集体议论这一关。那时“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政治挂帅”,人们敢说话敢拉脸,个人也脸皮薄,怕落个耍奸撒谎、懒惰自私的坏名声,本人或子孙说媳妇都难,为顾脸面也得积极劳动。
投工,不光给本生产队干,还给大队、公社,以及县和县以上更大范围干;不光干农活,还搞工副业,还当大队干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机手电工、代购代销,还搞治安保卫、民兵训练,还搞春节群众文艺演出,还参加公社以上各级党、团、妇、武、贫协、治安、民调等各类会议,还常年出动大批劳力参加根治海河及县社大队各级大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分怎么记?我所了解的方法是:(1)凡给大队以上出工,各生产队按上级分配出工劳力均衡相等的,大至根治海河、搞大型农田水利建设、民兵训练,小至修缮学校、大队部,维护村级道路,由本生产队照常记工。(2)凡属特殊出工,如大队干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机手电工的常年报酬,文艺排演,少数骨干人员重要工作、政治活动的临时报酬,各生产队出工不均衡,大队就暂记“社务工”,开条转到生产队记工。决算时,大队对所有生产队之间出社务工情况进行平衡,对出工多的生产队,大队自身有工副业收入的,由大队以现金的形式给其补偿多出工部分,无工副业收入的,由出工少的生产队,按全大队平均工值,以现金或粮食折算成钱补偿。规模小、“一层楼”即大小队是一个的村,不存在这个问题。(3)凡属到县以上开会,上级给发了误工补助的人员,回队后把钱交给生产队,照记工分。
集体经济时农民生活较普遍困难的原因究竟在哪里?从上述情况看,“平均主义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都不能够恰如其分、实事求是的概括当时集体经济实质和弊端。为什么农民还普遍地感到那时生活比较困苦和艰难呢?那时的苦,是农业总体收入不高造成的。上面已经提到,实行集体经济时,面临的是旧中国留下的,新中国正在加紧改造中的不断发生的水患灾害,低洼盐碱、易旱易涝的恶劣自然条件,没有化肥、优种,缺机少电,农业科学技术普遍缺乏落后的生产条件。那时亩产大都在二三百斤,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中期,随着农田基本建设作用的发挥和化肥的使用,情况有了改变,产量逐年上升,农民生活有所改善。以我队为例,1976年人均实际分小麦已由过去的90斤增长到150斤,也就是说小麦在全年360斤的口粮中占比已由90天增加到150天,但总体上还没有根本性改变。更重要的原因是,就粮食而言,政策规定不让多分,增产多少都难到社员手中;就劳动收入说,许多劳动产生的是社会效益和长远效益,是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不是当年当队直接分配的消费品。最近有网上回忆文章说的两句话,点到了问题的实质:“我们那时是一辈子吃了几辈子的苦,一辈子创了几辈子的业。”关键就在,那时的农民,不仅仅是为生产队内部的小集体成员搞了“平均”,以计划内的价格为人多劳力少的户提供了维持他们生活的粮油柴菜,承担了本应由国家和全社会承担的政策成本,而且所付出的劳动包括取得的成果,还办了许多大事,为国家、为民族、为后代、为未来做出了贡献,创下了基业。
——不仅从人力上,而且从财力上,为国家长期承担了大型水利建设等工程。如根治海河,应是国家的工程,每用一个工,都应由国家给报酬,所有工机具,都应由国家出,但国家基础差、底子薄,拿不出这些财力,只有让农民承担。全省长年百万民工战海河,每年每个生产队出动5到8名男整壮劳力,用自己或本队的工机具,一连十几年,春冬两季180天大干苦干。国家未给任何报酬,只是补一部分粮食,民工完全在本队记工分,参加本队分配,所留农活由在家劳力承担,本队还要为河工出粮、报销用费路费、记高出满工20%的工分。这是一笔巨大的负担和牺牲。粗算,此项当时每年为国家节省不下几亿,现在需几百亿。还有其他水利工程,如大型水库建设、公路建设等,也是如此。农民的这项付出没有得到当年可分配的产品,却是惠及全省及京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大业。根治海河的成功,还为沧州地区特别是东部盐碱地的根治,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沧州盐碱地面积大大缩小。
——在每年的劳动投入中,县社村队四级长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占了很大比重,为彻底改变生产条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沧州地区及所属各县社年年大搞“台、排、改、灌、林、路”齐抓,“旱、涝、碱、板、粗”综合治理的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群众运动,男女整半劳力往往全部出动,吃在地、睡在洼,吃自家的粗粮陋饭,干挑沟挖壕、装车推土最重的活,除了记工分,无有其它报酬,有的工程当年甚或几年见不到收益。代价和牺牲换来的是,大大改造了中低产田,实现了成方连片大面积的稳产高产。以至构成改革以来连续几十年农业丰收最基本的因素。
——着眼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不搞“分光吃净”,勒紧裤带积累集体财富。在每年的预留中,除留足种子、饲料、社务工粮、五保户口粮等,大多生产队都要留下少则两三千斤、多则上万斤的储备粮,以备不时之需。不少生产队过日子心强,搞工副业获得的利润以及出售粮棉油、瓜果菜肉畜等产品所得的现金收入,舍不得全部分给社员,积极用于购置大牲畜和农机具、办电等,增强生产队的经济实力。我所在的生产队到70年代,增添了两辆胶轮大车,告别了老辈子流传下来的木轮铁皮大车,可使役的牛驴也由12头增加到24头,骡马从无到有,存栏保持3头,饲养室、仓库、记工室从借房到在村里聚居区自建,占地约3亩,另购置了大量水车、水泵、柴油机 、电动机、铡草机、脱粒机,架设和添置了低压线路、电缆、电器等。这些设施设备,在集体经营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家庭承包后又为生产迅速启动提供了优越条件。
——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任务。不但夏秋两季,按时、按质、按量上交国家征购,完成上级下达任务,丰收年份还多交爱国粮,踊跃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所以新中国成立短短30年就建成一个门类齐全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农民所做出的牺牲功不可没。许多本应由国家承担的责任,如五保户、军烈属、鳏寡孤独老人的生活,民办教师的报酬,小学教学、管理费用,等等,一律由所在大队承担,最终全部由生产队分担。大队除“两委会”之外,青、妇、兵、贫、治、调六大群众组织一应俱全,会议和活动也过于频繁。仅春节期间由大队干部带领,党团员及基干民兵给军烈属、荣复退伍军人敲锣打鼓送春联送慰问信、挑水扫当院一项,几十人就得足足忙活两天。当时是突出政治、革命为先、不怕人工浪费、不计经济成本。农村改革后这类政治活动已基本少见或完全取消,许多基层组织也不复存在或名存实亡。当时这样做无疑也是加重农民自身负担的一个原因。但历史真实的告诉人们,正是这样做,才粉碎了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美梦,才制止了美苏两霸亡我中华的图谋,才维护和巩固了社会主义江山。
综上所述,实行家庭承包后农民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固然是同自己报酬挂钩紧密调动了群众生产积极性的结果,但与当年农民的付出创造的丰收条件,与国家实行重点转移压缩社会管理人力物力,与不再搞根治海河和农田基本建设等大型群众工程,与由国家承担的社会公益事业不再由农民承担,与不再限制分配且全部实行市场价格使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差”大大缩小,都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在回顾和总结这一历史时,只能说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做出的牺牲是客观要求,而简单地把苦难说成是由“大锅饭”造成的,并以此完全贬低或否定集体经济时期的分配形式是不客观全面的。
(作者:左德兴 沧州市贸促会原会长)
【忆昔话往】
回忆当年电影队
1957年春,河北省总工会无偿调拨给我场一部35毫米移动式电影放映机和1台发电机,并派来两名放映员,同年5月份建立了中捷友谊农场电影放映队。
我是1957年10月份调电影队工作的。那时电影队特别受人们欢迎。人们一听说“今天咱这里放电影”都喜笑颜开,孩子们都欢天喜地、成群结队地到村头迎候。天刚黑,银幕前就坐满了人。
那时,农场条件十分艰苦。放电影,夏、冬两季是我们放映员最难“熬”的季节。夏天蚊子咬,冬天冻得手脚麻木。除了总场部、一队至八队和村庄队有房子外,其余的地方,人们都是住席棚和窝铺。
记得1957年冬天,我和两名同事到畜牧队(今十二队附近)放电影。那天,西北风很大,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把银幕挂起来,不一会儿就被大风刮倒了。刮倒了又挂起来,电影刚放映到半截,银幕又被刮倒了,再重新挂起来,坚持把电影放完。电影放完后,由于住处紧张,我被安排在一个做木工活的工栅里住下,夜里冻得睡不着觉,腿肚子抽筋。
1958年8月的一天,我们到原六分场(今南港)放电影。由于雨水大,旱路不能走,六分场工会主席亲自带领两只小船来接我们,在六分场放映了四五场电影。当到了二十四队时,却遇到麻烦,队部的四周一片泥泞,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放映场所,只好把银幕挂在两面环水的渠埝上。电影终场后,我们找不到往宿的地方,只好在渠埝上露宿。没有蚊帐,大个的黑花蚊子发疯似地叮咬我们,我被咬得浑身是包,痛痒难忍,就往身上抹汽油,结果不光不起作用,还把皮肤烧红了。
当年,中捷农场电影队在地区电影发行部门和放映单位的同行中享有较高信誉,一是做到影片无损伤,完好率高;二是按时周转,不误片期,可信度高。然而做到这两点并非易事,尤其是后者,难度更大。
那个时候,农场到沧州是土路,雨季往往不能通车。可是影片到规定期限无论有什么情况也得按时送回,否则要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所以,遇到阴雨天气就苦了我们,只有骑自行车或骑马送片。比如,1962年七八月间,我们刚在礼堂放完《林海雪原》就下起了大雨。从农场到黄骅的路上满是水,不能通车。按规定必须把影片送到沧州新华礼堂。第二天上午9点,我骑上自行车驮上影片就出发了。一路上骑一会儿,推一会儿,终于在下午4点赶到了沧州。这时候,新华礼堂已经售出了票,只等着影片到来。当他们正担心水大路远难以送到而焦急不安时,我把片子送到了。类似这种情况经历了多次。
农场电影队不仅在全区享有较高的声誉,还受到国际友人的赞誉。1960年10月下旬,捷克驻华使馆二等秘书邓纳和夫人以及商务参赞普拉哈斯卡、翻译等一行4人来我场参观。农场领导决定为客人举行电影招待会。事不凑巧,几天前,电影队长徐群及其爱人(放映员)到天津探亲未归,这时电影队就我一个人,按规定双机放映必须由两人操作。现在由我一个人操作两部机子,我心里没有底。为了圆满完成放映任务,我用了半天时间把影片的每一个破齿孔都进行了修补,对机器进行了认真保养。那天放映的是彩色影片《笑逐颜开》。直到银幕上出现“剧终”二字,我才松了一口气。放映结束后,邓纳和翻译走进放映室,当他们看到只有我一个人操作时,感到吃惊,亲切同我握手并竖起拇指用流利的中国话称赞道:“放映得很成功,谢谢你!”
(作者:熊寿华 中捷农场工会退休干部)
